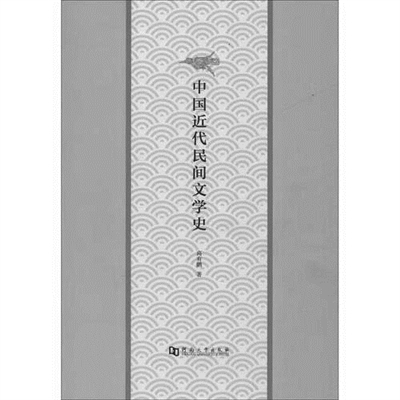
高有鹏是“一棵结大果子的树”。块头之大,是闻名遐迩的“文坛壮汉”,身高体重做业余队篮球中锋绰绰有余;影响之大,在央视百家讲坛疾呼“保卫春节”,声振屋瓦;境界之大,毅然提出“神话群”“语域”“新神话主义”“神话美学”等概念;手笔之大,无论小说还是学术著作,出手就是上百万字;描绘《清明上河》,演绎《大宋风月》,挥洒《大篆论语》。
然而,看到他刚刚出版的、积四十多年的学术积累的、十二卷三百六十万字的“大著”《中国民间文艺思想史论》(宁波出版社),再看看网络报道之际他的近照,作为老兄的笔者不无难受:几年不见,他脖子长了,腰围细了,瘦了几十斤。
一、从文学潜入民俗
“文化的底色”“夜来风雨声”“诗与酒”“飞龙在天”……看着《中国民间文艺思想史论》那“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笔者不能不记起高有鹏的老师也是笔者的恩师张振犁先生。
“中原神话的拓荒者”张振犁先生是钟敬文先生的高足、全国民间文艺学终身成就奖得主——九十五岁还出版了多卷本《中原神话通鉴》——也是有鹏兄的毕业论文《河南现代民间文学史》的指导老师。
从吾侪入学至今几十年来,“民间文学”在高校的地位均不能算高。学术格局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总是“三巨头”,民间文学在“边缘地带”叨陪末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创作与“新方法论”批评崛起之后,大家才日益窥见“文学”与“民俗”“民间”的血肉联系。而母校河南大学恰恰又是民间文学的重镇之一。早在20世纪初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期,就有郭绍虞的谚语研究,罗根泽、白寿彝的民歌研究,董作宾的民俗文学研究。30年代则有江绍原的民间文学研究,姜亮夫的敦煌文学研究,高亨的神话研究,朱湘民歌研究。张振犁老师作为钟敬文先生的高足,带领弟子遍走中原大地,开创了中原神话学派。康保成、廖奔、孟宪明、陈江风等,都是领风骚的一代天骄。就这样,高有鹏从一个单纯的中文系学生,很快地进入了民俗学研究的“庙堂”,格局逐渐扩大,视野愈发开阔,成就如日中天。
高有鹏潜入民俗的“投名状”是中原庙会研究。
苏东坡曰:“庙前行客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古庙会,熙熙攘攘,香烟缭绕,高有鹏凭直觉意识到:这是一处极具价值的文化矿藏。他瞄准了与远古大神崇拜联系密切的庙会,晋、冀、鲁、豫、湘、粤、云、贵、川,都印满了他的足迹。1999年,他的《中国庙会文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荣获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在扉页恭恭敬敬写下:“谨以此书敬献给张振犁先生”。张振犁先生对他情同父子,后来他每出版一本书,都会郑重呈送。
二、从历史切入民间
高有鹏的另一位恩师华锺彦先生多次叮咛弟子:要做学问,先治经史。这八个字,有鹏几十年来奉为圭臬。
二十多年前,笔者尚在报社做记者,回母校采访,拉着师兄孟宪明,居然与有鹏聊了个通宵。彼时三十出头的他,居然要写一部“中国民间文学通史”——打通古代、近代、现代。彼时,我以为大师兄是在“画大饼”:以一己之力完成此浩大的工程,仅仅史料一项,需要几多精力?不料15年之后的2015年,16开布面精装、500多万字、重达10公斤的《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由线装书局出版。惊愕之余,笔者能够做的,是在自己主编的大学学报上组织一期各路专家的讨论。
如今又是八个年头,有鹏从中原南下上海,执教上海交大,原以为他可以吃吃老本,做博导,授业解惑,直至退休。没想到他还是念兹在兹,再折腾出这一套《中国民间文艺思想史论》——由庙会的“点”,到通史的“面”,从史料的撷取,到文艺思想的流变,论从史出,史自“思”来。
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评论郑振铎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说郑著材料很丰富,但观点含糊。我想,有鹏兄之所以要在“通史”即发展史之后,再出“思想史”者 ,核心恰恰在“史识”而非“史料”也。
果然,他发来的长微信说得明白——
“我多次病中苦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和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二十五史别史》等典籍包括《二十二子》等百家文献!我更看重地域文化如一些方志。我想表现人民大众特别是更多底层民众文化的思想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这是很艰难的尝试。古文献很多而选择有限,只有侧重典型性和人民性,以人民大众为主体,历史上的传统文献,多半都是摒弃‘野’与‘俗’,其实是忽略了文化思想创造的大主体,是过分强调精英特殊性的个体,忘记了社会各阶层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整体。”
“文化是文明的具体展现,是历史沉淀的特殊的思想。没有面对天地人而形成的思想——即各种意识和观念的集合,就无法认知文明与文化的客观实在。尤其需的是,从历史的本体,挖掘与体验人民思想即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此,文献的静态与生活的动态是合体的。”
在这里,有鹏提出的是“中华民间文艺的整体观”——即把中国民间文艺的不同历史阶段,视作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整体,即把对于前人的继承、相比于同代人显示的特质、对后代人的影响三个基本点合而为一,以便于读者全面理解中国文化,领会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与深刻性。
李泽厚先生35年前就倡导说:“中国大小传统之间、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相距并不悬隔(如对比西方),而经常渗透交融。这无疑是对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紧相联系的特点,对统一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等大有影响,而颇值得探究,特别是值得首先从民间文化的实证的微观研究来考察和思考。”我想,有鹏兄正是这种“交融”论最为坚定而且最有成效的践行者。
三、让民间文艺史对接马克思主义
必须补充的是,2021年,有鹏已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上海交大出版社)一书。笔者在《人民政协报》上看到了国务院参事室孟云飞先生的推介,说此书的文化立场有五个层面:一是人类文明的视野,认为中国作为人类文明集中的汇聚点,表现出恒久的文明脉络和与人为善等民族传统。二是中国传统的丰富性,如“礼失求诸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欲灭其国先毁其史”等问题的重要意义。三是历史的现实性,以民众情感为文化发展依据,打破简单的精英至上理论。四是民族平等理论,倡言相互尊重、相互融合,体现博大胸怀——如中国汉字吸收的人类文明。五是中国文化的生活属性,把信仰与审美作为文化的核心。全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好教材。
而有鹏论述《中国民间文艺思想史论》视角之际说:“平视世界是本书的重要追求,强调和突出的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以面向大世界大文化大思想大视野摆脱盲目性和短视性!”他说相比之下,自己更愿意回到马克思的原著,同时结合中国文化的实际:“我不是为出书而写作,而是追求基层和底气,理论要联系实际。”
高有鹏把中国民间文艺的历史发展、思想含量、哲学特质、精神价值与文化自信的展示、中国故事的讲述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不言而喻。







